这是昨天,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刚和老朋友乔治·加兰吃完中饭。仆人给他送来一封用封蜡封口、贴着外国邮票的信。
乔治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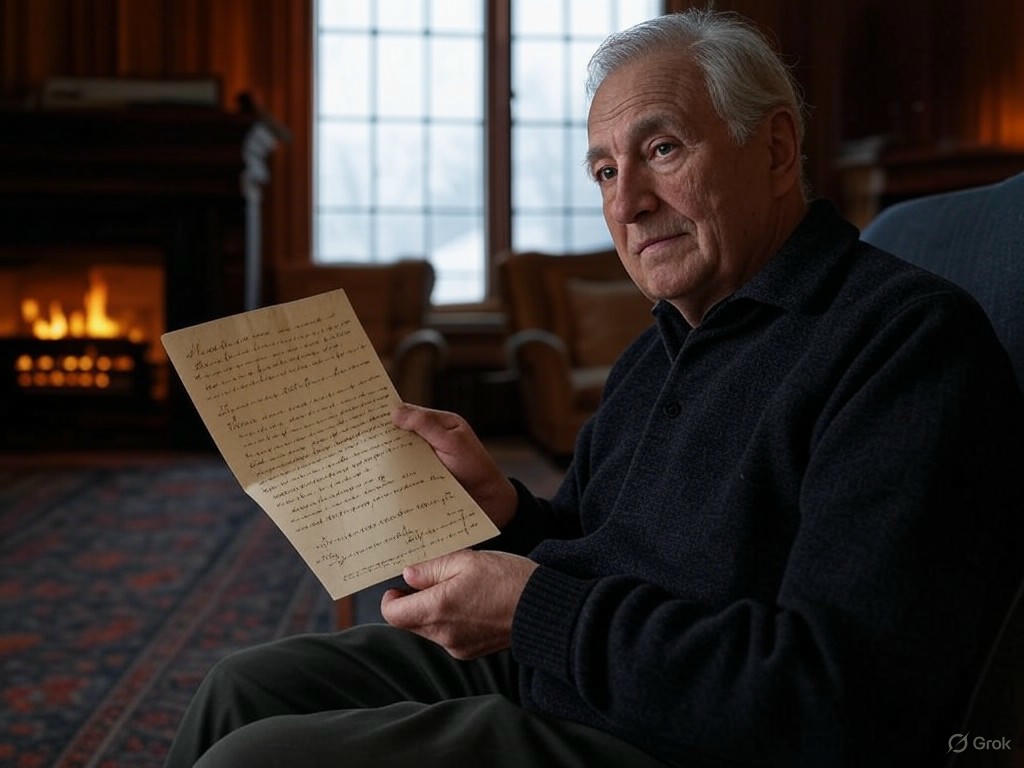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
他开始看那用龙飞凤舞般的粗大英国字体写的八页信。他怀着对触动您心弦的事才会有的那股兴趣,郑重其事地慢慢看着。
接着他把信放在壁炉台的一个角上,说:
瞧,这儿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跟您讲起过的有趣故事,然而也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爱情故事!啊!那一年的元旦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元旦。一转眼已经有二十年了……是呀,我那时三十岁,而我现在已经五十岁了!……
我当时是在我今天主持的这家海上保险公司里当检查员。我已经打算好在巴黎度过元旦这个节日,既然这一天已经被公认为节日,没想到突然接到经理的一封信,吩咐我立即动身到雷岛(2)去,有一艘在我们公司保过险的圣纳泽尔(3)的三桅帆船刚在那儿搁浅了。当时是上午八点钟。我十点钟到公司接受指示;当天晚上我乘上快车,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了拉罗舍尔(4)。
在登上开往雷岛的船让一吉通号以前,我还有两个小时,于是在城里兜了一个圈子。拉罗舍尔真是一个古怪的、极其富有个性的城市,街道纵横交错,像座迷宫,两边的人行道在没有尽头的长廊下面朝前伸展,很像里沃利街的那种有拱顶的长廊,但是很低很低。这些长廊和这些神秘的低矮的拱顶,仿佛是作为阴谋分子的布景,作为从前的战争的,英勇又野蛮的宗教战争的,既古老陈旧而又激动人心的布景建筑起来并且留存至今的。这是胡格诺派(5)的古老城市,森严,闭塞,没有任何使鲁昂变得那么宏伟壮丽的、令人赞赏的纪念性建筑物,但是由于它那整个森严可畏的,还带着一点儿阴沉的外貌而引人注目。这是一个属于不屈不挠的好争好斗的人的城市,狂热在这儿必然会产生,加尔文派(6)教徒的信仰就曾经在这个城市里热情高涨,四军士的阴谋(7)就曾经在这个城市里诞生。
我在这些古怪的街道上闲逛了一会儿,登上了一艘鼓肚子的黑色小轮船,它应该把我送到雷岛。它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喘着气离岸,在两座护卫港口的塔楼中间经过,穿过锚地,出了黎塞留(8)建筑的防波堤,齐着水面可以看见防波堤的那些庞大的石块,像一条巨大的项链环绕着城市;然后朝偏右方向驶去。
这是那种使人心情沮丧,把人的思想压垮,把人的心束紧,让我们的体力和精力完全失去的阴沉沉的白天;是一个灰,冷冰冰,被浓雾弄得十分肮脏的白天,像雨水一样潮湿,像霜冻一样冷,像阴沟里蒸发出的水汽一样闻起来有一股臭烘烘的气味。
在这层低矮而阴沉的雾顶底下,黄色的海水,淹没这些无边无际的海滩的含沙的、不深的海水,没有一丝波纹,没有一点变动,没有生命,是一片由泥水,油腻的水,停滞的水汇积而成的海水。让-吉通号在上面经过,惯常略微有一点摇晃,它切开这一大片不透明的、光滑的水面,接着在后面留下一些轻微的波浪,一些轻微的汩汩声,一些很快就恢复平静的轻微的起伏。
我开始和船长聊天。船长是一个腿短得几乎没有的小个儿,像他的船一样圆,也像他的船一样摇晃。我想了解一些关于我去调查的那次海难的详情细节。一艘圣纳泽尔的大三桅横帆船,玛丽-约瑟号,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搁浅在雷岛的沙滩上。
船主信上说,狂风暴雨把这艘船抛得那么远,已经不可能使它脱浅,因此不得不尽快把能卸下的东西全都卸下搬走。因此我应该察看出事船只的情形,估计它在失事前的状况,并且对为了使它重新浮起来,是否尽到了一切努力做出判断。我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前来,是为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在诉讼中以对审方式出庭作证。
经理在得到我的报告以后,应该采取他认为必要采取的措施,来维护我们公司的利益。
让-吉通号的船长对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因为他曾经被要求带着他的船去参加抢救的尝试。
他把这次海难讲给我听,经过其实很简单。玛丽-约瑟号被狂风刮着,在黑夜里完全迷失了方向,在一个白浪翻滚的大海上——“牛奶浓汤般的大海,”船长这么说——盲目地航行,来到这些广阔的沙洲上搁了浅,这些沙洲在低潮时把这个地区的海岸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撒哈拉沙漠。
我一边聊天,一边朝周围看,朝前面看。在海洋和低沉的天空之间还留有一片无遮无拦的空间,肉眼可以看得很远。我们沿着一片陆地航行。我问:
“这就是雷岛吗?”
“是的,先生。”
船长突然朝我们前面伸出右手,指着大海里的一样难以觉察的东西让我看,并且对我说:
“瞧,那就是您的船!”
“玛丽-约瑟号?……”
“当然。”
我一下子愣住了。这个几乎看不见的黑点子,我会把它当成一块礁石,看上去离海岸至少有三公里。
我接着又问:
“但是,船长,您指给我看的那个地方水深大概有一百寻(9)吧?”
他笑起来了。
“一百寻,我的朋友!……老实告诉您吧,不到两寻!……”
他是波尔多人。他继续说:
“现在九点四十分是高潮。到王太子旅馆吃顿中饭,然后您双手插在口袋里在海滩上走着去,我向您保证,两点五十分,至多三点钟您就可以连脚也不湿地到达失事船只那儿,我的朋友,您有一个钟头四十五分钟到两个钟头可以待在上面,听好,不能再多;否则您就会给困住。海水,它退得越远,回来得也越快。这片海岸非常非常平坦!四点五十分您开始往回走,请相信我;七点半您再乘上让-吉通号,今天晚上把您送到拉罗舍尔的码头。”
我谢过船长,到轮船的船头上坐下,观看我们迅速接近的圣马丹(10)这个小城。
它和所有那些充当沿着陆地散布的贫瘠岛屿的首府的微型港口完全一样。这是一个大渔村,一只脚在水里,一只脚在陆地上,吃的是鱼和家禽,蔬菜和贝类,萝卜和淡菜。岛非常低,耕种的土地很少,然而人口好像很稠密;不过我没有深入到村子里。
吃完中饭,我越过一个小岬角,接着因为海水迅速地退下去,我穿过沙滩,朝着我远远看见的像是一块突出水面的黑色岩石的东西走去。
我在这片像肌肉一样富有弹性的,而且仿佛在我脚底冒汗的黄色平原上走得很快。大海刚才还在这儿,现在我远远地看见它,几乎逃到了视野以外,那条把沙滩和海洋分开的界线我已不再看得清楚。我相信亲眼看到了一个广阔的、超自然的仙境。大西洋刚才还在我面前,接着在沙滩上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舞台布景从活板里消失一样,现在我是在一片沙漠中前进。只有感觉,咸海水的气息,还留在我的心里。我感觉到了海藻的气味,波涛的气味,海滨的那种既强烈而又好闻的气味。我走得很快;我不再感到冷;我望着搁浅的失事船只,随着我继续前进,它变得越来越大,现在很像一条遇难的巨鲸。
它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在这一大片辽阔平坦的黄沙上,体积看起来大得惊人。走了一个小时以后我终于来到它的跟前。它侧身躺着,裂开了,破碎了,露出像野兽肋骨一样折断的骨头,它的被大铁钉穿透的、涂了柏油的木质骨头。沙已经侵袭它,从所有的裂缝钻进去;沙抓住它,占有它,再也不会放开它了。它看上去好像已经在沙里生根。船头深深地扎进这片温和而又凶险的海滩,船尾却翘起来,仿佛在朝着天上发出一声绝望的呼叫,把黑色船壳板上的“玛丽-约瑟”这四个字投向天空。
我从最低的一边爬上这艘船的尸体,接着到了甲板上,钻进船舱。阳光从被打破的翻板活门和船侧的裂缝透进来,凄凉地照亮了这些又长又暗、和地窖相差无几的地方,到处是被毁坏的细木护壁板,除了黄沙,里面什么也没有,黄沙充当了这木板地道的地面。
我开始摘要地记下船的状况。我坐在一只破了的空琵琶桶上,就着从一条宽阔的裂缝透进来的亮光写着,从这条裂缝我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海滩。由于寒冷和孤寂,时不时有一阵奇怪的颤栗传遍我的全身,我常常停下笔来听出事船只上的隐隐约约的神秘响声:螃蟹用它们的钩形爪子搔船壳板的声音,已经在这个尸体上定居的无数大海里的小生物的声音,还有船蛆的轻微的、有规则的声音;船蛆发出钻子般的吱吱声,不停地蛀蚀着被它们挖着吃着的老船架。
猛然间我听见离我很近有人声。就像遇到幽灵出现,我一下跳了起来。有一瞬间我真的相信会看见从阴森森的货舱的舱底站起来两个淹死的人,向我叙述他们是怎么死的。当然,我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利用腕力爬上甲板;我看见在船头前面站着一位高个子的先生和三位年轻的姑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带着三个密斯。在这艘废弃的三桅帆船上忽然看见冒出我这么个人来,可以肯定他们比我还要害怕。最小的一个姑娘撒腿就逃;其余两个姑娘一把抱住她们的父亲;至于他,他张开了嘴;这是他流露出他的激动情绪的唯一表示。
接着,在几秒钟以后他说:
“噢,相(先)生,宁(您)是这艘海船的主人吗?”
“是的,先生。”
“我冷(能)够参观吗?”
“能,先生。”
他接着说了一句很长的英国话,我仅仅听出了这个词:gracious(11),它接连出现了好几次。
他想找一个地方往上爬,我把最合适的地方指点给他,并且朝他伸出手去。他爬上来;然后我们帮助三个已经放下心来的姑娘。她们很可爱,特别是大的一个,一个十八岁的金黄头发女郎,鲜艳得像一朵花,而且那么清秀,那么娇美!说真的,漂亮的英国女人看上去非常像大海里鲜嫩的产品。人们会说这个英国女人刚刚从沙子里出来,她的头发保留着沙子的色泽。她们娇嫩鲜艳,使人想到那些粉红贝壳的柔和色彩,想到在海洋的未知深度下产生出来的那些珍奇的、神秘的光彩夺目的珍珠。
她的法语比她父亲说得稍微好一些,便充当我们的翻译。必须详详细细地叙述船只遇难的经过,我信口编造,编造得就像发生这场灾祸时我亲身在场似的。接着这一家人全都下到出事船只的舱内。他们刚钻进这勉强被照亮的、阴暗的坑道,就立刻发出一声声惊奇和赞赏的叫喊;忽然间父亲和三个女儿都拿出了毫无疑问藏在他们宽大的雨衣里的画册,同时开始用铅笔对着这凄凉而古怪的地方画四幅速写。
他们并排坐在一根凸出的大梁上,四本放在八个膝头上的画册上画满了细小的黑线条,表现的应该是玛丽-约瑟号的裂开的肚子。
姑娘中最大的一个一边画,一边跟我聊天,而我呢,则继续检查船的骨架。
我知道了他们在比阿里茨(12)过冬,特地赶到雷岛来看看这艘陷在沙子里的三桅帆船。这些人一点也没有英国人的那种傲气,他们是一些纯朴的、善良的疯子,是布满全世界的那种来自英国的永恒的漂泊者。父亲又高又瘦,红通通的脸颊围绕着白颊髯,活生生是块三明治,切成人头形的一段火腿夹在两小片毛垫子中间。女儿们腿长,像正在发育生长中的小涉禽,她们也很瘦,大的一个除外,而且三个人都很可爱,不过大的一个特别可爱。
不论是讲话,叙事,笑,理解或是不理解,还是抬起眼睛——一双像深水一样蓝的眼睛——问我,停下画笔猜测,重新动手画画,以及说“yes”(13)或者“no”(14),她都有一种那么古怪的表现法,致使我会永无尽期地去听她,看她。
突然间她低声说:
“我听见这条船上有轻轻的响动声。”
我仔细听,立刻听出一种奇怪的、连绵不断的轻微的响声。这是什么声音?我立起来,过去朝裂缝外面张望,不由得发出一声猛烈的叫喊。海水已经逼近我们,快把我们包围起来了!
我们立刻到甲板上面去,已经太迟了。水已经把我们围住,并且以惊人的速度朝海岸奔跑。不,它不是在奔跑,是在滑动,是在爬,是像一块巨大的污迹在延伸。沙滩上还刚有几厘米深的水,但是那条难以觉察的涨潮的逐渐远去的界线已经看不见了。
英国人想往下跳。我把他拦住,逃走已经不可能,因为我来时不得不绕过一些深水潭,往回走很可能掉进去。
在我们心里有过一分钟的可怕的惶恐不安。接着英国姑娘开始露出笑容,低声说:
“我们成了遇难的人!”
我想笑,但是恐惧完全控制住了我,一种怯懦的、可憎的、像这潮水一样卑劣和阴险的恐惧。我们遇到的种种危险同时出现在我眼前。我恨不得大声喊叫:“救人啊!”但是,朝谁喊叫呢?
两个英国姑娘躲在她们的父亲身边。她们的父亲惊慌失措地望着我们周围的茫茫大海。
黑夜像大西洋的潮水上涨一样快地降临,一个阴沉的、潮湿的、冰冷的黑夜。
我说:
“只好留在这条船上了,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英国人回答:
“噢!yes!”
我们在那儿待了一刻钟,半小时,说真的,我不知道周围的这片黄水我们看了有多少时候。这片黄水变得越来越浓厚,它在旋转,仿佛沸腾了,仿佛在被它重新夺回的无边无际的沙滩上玩耍。
姑娘中有一个感到冷,我们打算重新下去躲避海风,海风虽然轻微,但是冰冷冰冷,吹到身上,像针一样扎着我们的皮肤。
我朝翻板活门俯下身去。船舱里已经满是水。因此我们只好蜷缩身子紧靠着船尾的船壳板,这样多少可以挡住一点寒风。
黑暗这时候已经把我们笼罩,我们在阴影和水的包围下,互相紧紧地挨在一起。我感到英国姑娘的肩膀挨着我的肩膀在颤抖,她的牙齿不时地格格作响;但是我隔着衣服也感到了她身体的温暖,这种温暖我觉着就像吻一样甜美。我们不再说话,像刮飓风时蹲在沟里的野兽那样,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待着。然而尽管如此,尽管长夜漫漫,尽管危险十分可怕,而且有增无已,我开始感到自己在这儿很幸福,因为寒冷和危险而感到幸福,因为在这块船板上,离着这个漂亮的、娇媚的姑娘这么近地度过的这些漫长的、充满黑暗和焦虑的时刻而感到幸福。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会有渗透我全身的这种舒适而愉快的奇怪感觉。
为什么?谁知道呢?是因为她在这儿吗?她,是谁?一个不相识的英国姑娘吗?我并不爱她,我一点都不认识她,而我却感到自己心动了,被征服了!我想要救她,为她做出牺牲,干出种种傻事吗?真是怪事!一个女人的在场怎么会使我们的心乱到这个地步?是她那优雅风度的魅力使我们倾倒了吗?是美貌的和青春的诱惑力像葡萄美酒一样使我们陶醉了吗?
还宁可说是一种爱情的,神秘的爱情的接触?它不断地力图把人结合在一起,它把男人和女人面对面放在一起以后,就立刻发挥它的力量,使他们心里充满了激动,一种混乱的、秘密的、深邃的激动,就像湿润大地,让鲜花在上面长出来一样!
但是黑暗中的寂静,天空的寂静,变得可怕起来,因为我们隐隐约约听见我们四周围有一种绵延不断的轻微响声,低沉的大海涨潮的訇訇声,水流冲击着船身的单调的啪啪声。
突然间我听见了呜咽声。英国姑娘中最小的一个哭了。她的父亲想安慰她,他们开始用他们的语言交谈,我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能猜测到他是在安她的心,而她仍旧感到害怕。
我问我身旁的姑娘:
“您不感到太冷吧,密斯?”
“啊!不,我刊(感)到非常冷。”
我想把我的大衣给她,她不肯要,但是我已经脱下来,不顾她拒绝,披在她身上。在短暂的争执中,我碰到了她的手,我的全身上下不由得打了个愉快的哆嗦。
几分钟来,空气变得更凉了,水冲击船身的啪啪声也变得更响了。我立起身来,一阵大风吹到我的脸上。
起风了!
英国人和我同时发觉,他仅仅说了一句:
“这对我们来说很曹(糟),这……”
当然很糟,如果起浪,哪怕是轻微的海浪冲击和摇撼这条失事船只,死亡可以说是肯定无疑的事,因为这条船已经损坏、断裂得那么厉害,只要一个稍微猛烈一点的浪头就会把它打得稀巴烂,把它卷走。
我们的焦虑于是随着一阵比一阵强烈的狂风在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现在海上已经稍微起了一点波浪了,我看见在黑暗中有一条条白线出现后又消失,是浪花形成的白线,同时一个接一个的海浪冲击着玛丽-约瑟号的船架,摇得它一阵阵短促地颤动,这颤动一直深入我们的心里。
英国姑娘在打哆嗦;我感觉得到靠在我身边的她在颤抖,我恨不得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远远地,在我们前面,左边,后面,有一些灯塔在海岸上发出亮光,一些白的、黄的、红的、旋转的灯塔,宛如一只只巨大的眼睛,巨人的眼睛,在望着我们,在窥伺我们,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消失。它们中间的一座特别使我生气。它每隔三十秒钟熄灭一次,紧接着又亮起来。这一座确实是一只眼睛,眼皮不断的垂下,盖住它那炯炯的目光。
英国人时不时擦着一根火柴看看时间,然后把表放回到口袋里。突然间他越过他的女儿们的头顶,无比庄严地对我说:
“相(先)生,我祝您新年快乐。”
午夜十二点整。我向他伸过手去,他握了握我的手以后说了一句话,突然他的女儿们和他开始唱God save the Queen(15),歌声在黑暗的空气中,在寂静的空气中上升,穿过空间逐渐消失。
我一开始想笑;接着我被一种强烈的、奇怪的激动情绪所控制。
这首遇难者的歌,死刑囚犯的歌,有点儿不祥和壮丽,有点儿像祈祷,还有点儿更加伟大的性质,有点儿可以和古代的、崇高的Ave Caesar,moriturite salutant(16)相比。
他们唱完以后,我请求我身边的姑娘单独唱一首叙事歌曲,一首传奇歌曲,她愿意唱的任何一首歌曲,为了使我们忘掉我们的忧虑。她同意了,她的清脆、年轻的嗓音立刻在黑夜中飞翔。她唱的毫无疑问是一首哀伤的歌,因为那些音符拖得时间很长,缓慢地从她嘴里吐出来,像受伤的小鸟在波涛上面飞舞。
海浪汹涌澎湃,现在不断冲击着我们的失事船只,我呢,我只想着她的歌声。我也想到塞壬(17)。如果有一条小船在我们旁边经过,那些水手会怎么说呢?我的充满忧虑的心灵迷失在梦想之中:一个塞壬!这个把我留在这条被虫蛀蚀的船上,等一会儿将和我一起沉没在波涛里的海的女儿,她不真的是一个塞壬吗?……
但是我们五个人突然滚倒在甲板上,因为玛丽-约瑟号的右侧坍下去了。英国姑娘跌倒在我身上,我把她一把搂住,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只以为我的最后一秒钟已经来临,发疯似的连连吻她的脸蛋,她的太阳穴,她的头发。船不再晃动,我们也不动了。
父亲叫了一声“凯特!”我抱着的那个姑娘回答“yes”,她动了一下,挣脱身子。当然这时候我情愿船裂成两半,和她一起落到水里去。
英国人又说:
“一次小小的摇晃,没什么。我的三个女儿平安无事。”
他看不见大女儿,起初还以为她掉下去了呢!
我慢慢地重新站起来,突然间我发现海上有灯光,离我们很近。我叫喊,有人回答。这是一条来找我们的小船,旅馆老板预感到我们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来。
我们得救了。我却感到遗憾!人们把我们从破船上接走,送回圣马丹。
英国人现在搓着双后,低声说:
“美味可口的晚餐!美味可口的晚餐!”
我们确实吃了晚餐。我并不快活,我怀念玛丽-约瑟号。
第二天,在许多次拥抱和答应通信的许诺以后,不得不分手了。他们动身去比阿里茨。我差点儿跟了他们一起去。
我堕入了情网,我几乎要向这个姑娘求婚。如果我们在一起过上一个星期,我肯定会娶她做妻子!人有时候多么软弱,多么不可理解啊!
两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听人说起过他们;后来我接到一封从纽约寄来的信。她已经结婚,在信上告诉了我。从那时起我们每到新年都通信。她谈到她的生活,她的孩子,她的妹妹,从来没有谈起过她的丈夫!为什么?啊!为什么?……而我呢,我只和她谈玛丽-约瑟号……她也许是我唯一爱过的女人……不……唯一可能爱过的女人……啊!……是呀……谁知道呢?……环境左右一个人……接着呢……接着呢……一切都过去了。她现在一定也老了……我不会认出她来了……啊!从前的那个她……失事船只上的那个她……怎样一个美若天仙的……人儿啊!她信上说她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我的天主!……这使我感到痛苦得难以忍受……啊!她的金黄色的头发!……不,不,我的那个她已经不复存在……这一切……多么可悲啊!……
郝运 译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的《高卢人报》。同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小萝克》。
(2) 雷岛:法国夏朗德滨海省大西洋中沿海岛屿,与拉罗舍尔隔海相望。
(3) 圣纳泽尔: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港口城市,在卢瓦尔河口。
(4) 拉罗舍尔:法国西部夏朗德滨海省省会,滨大西洋海港城市。
(5) 胡格诺派: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形成的派别。多数属加尔文派。一五六二年至一五九八年间,曾与法国天主教派发生胡格诺战争。自一五五四年起加尔文教义在拉罗舍尔这个城市里占了强大地位,胡格诺派教徒几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五七三年安茹公爵(后来的亨利三世国王)未能攻破它的城防。但是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二八年红衣主教黎塞留战胜了市长吉东的顽强抵抗。
(6) 加尔文派: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加尔文(1509—1564)的思想为依据的各派教会的统称。法国胡格诺教派也是其中之一。
(7) 四军士的阴谋:以推翻法国复辟王朝(1814—1830)为目的的许多密谋之一,参加者是驻拉罗舍尔的军队的四名军士,他们是烧炭党人。密谋被破获后,他们于一八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巴黎被处死刑。
(8) 黎塞留(1585—1642):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宰相,红衣主教。执政期间取消胡格诺派的政治特权,惩治叛乱贵族。
(9) 寻:旧水深单位,一法寻约合1.624米。
(10) 圣马丹:雷岛北海岸市镇,是渔港和海水浴疗养地。上面提到的王太子旅馆是作者杜撰的。
(11) 英语,意思是:亲切的,客气的。
(12) 比阿里茨: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滨大西洋海滨城市,在拉罗舍尔的南边,也是海水浴疗养地。
(13) 英语,意思是:是的。
(14) 英语,意思是:不。
(15) 英语,意思是:上帝保佑女王。这是英国的国歌。
(16) 拉丁文,意思是:别了,恺撒,去战死的人向你致敬。据古罗马传记作家苏托尼厄斯(约69—约140)说,这是古罗马角斗士在角斗前列队经过皇帝包厢前面时叫喊的话。
(17) 塞壬: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女妖,住在地中海小岛上,常以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毁灭。